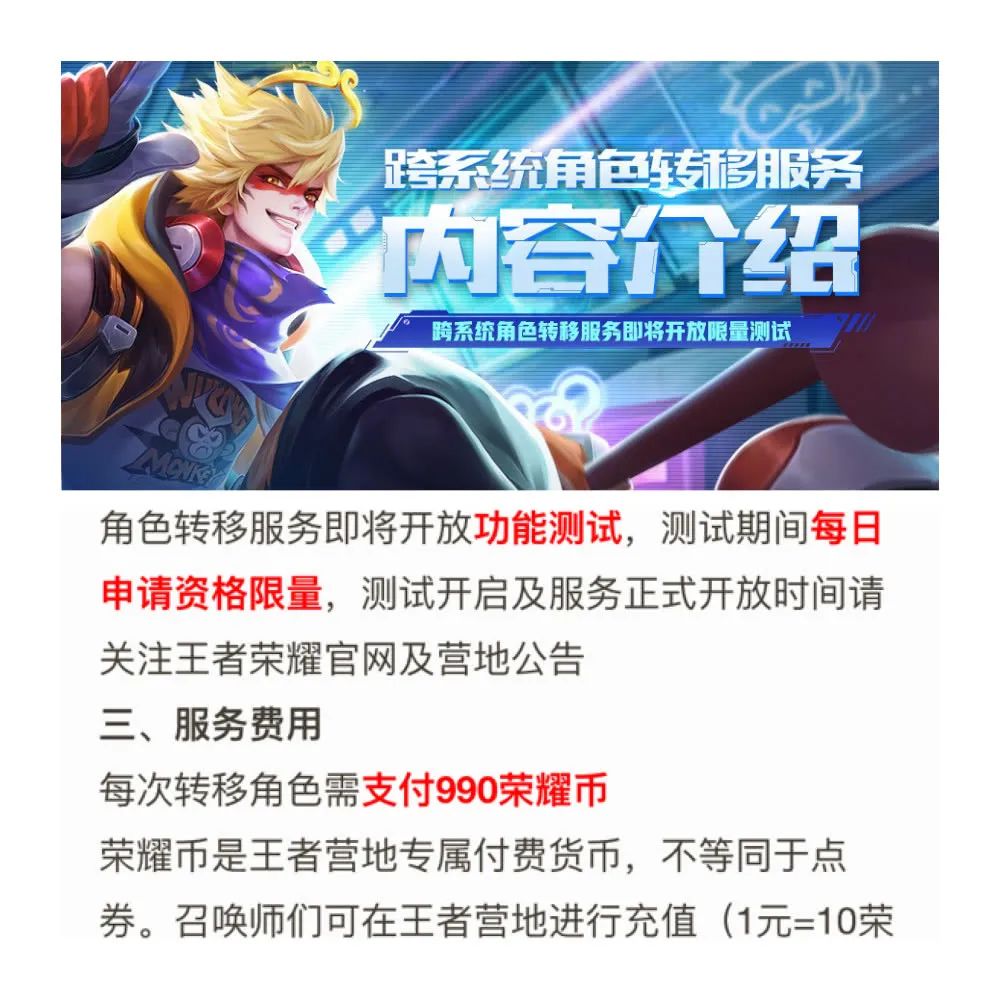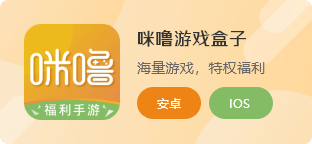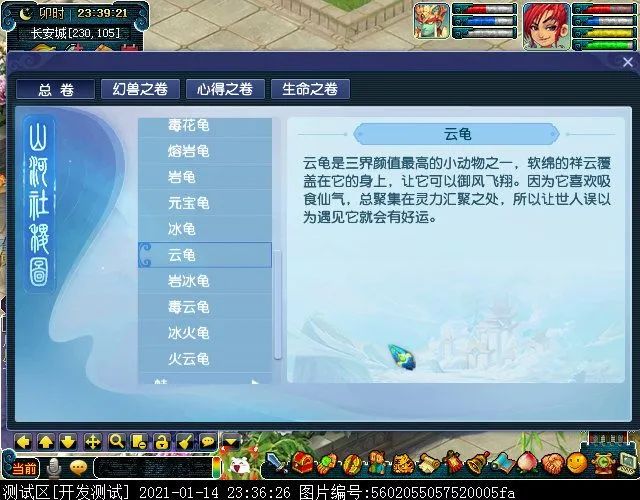1948年的冬天,13岁的高秉涵攥着母亲塞的半块玉米面饼,跟着逃难的人群挤上厦门开往台湾的货船。船舷外的海风吹得他直打哆嗦,他望着越来越远的大陆海岸线,耳边反复响着母亲的话:“儿啊,活下来,娘等你活着回来。”这句话像根“救命绳”,陪他熬过了台北街头的流浪,熬过了夜校的煤油灯,熬成了法庭上逻辑清晰的“高律师”——可乡音没变,胃里的“山东胃”没变,连做梦都在啃母亲做的煎饼。

真正把“回家”变成“终身任务”的,是1989年同乡会的那顿酒。几个头发全白的老兵拉着他的手哭:“秉涵,我们这帮老东西怕是熬不到回家那天了。你最小,万一有机会,把我骨灰带回去——埋在村口老槐树下,我要闻闻老家的麦香。”那天晚上,高秉涵翻出母亲1979年寄来的旧布衫(信里说“娘到死都攥着这个”),突然懂了:这些老兵的骨灰坛里,装的不是骨头,是攒了一辈子的“回家梦”。

1991年春天,高秉涵第一次踏回大陆土地。他怀里揣着3坛骨灰,手里攥着母亲的布衫,在菏门外的老槐树下跪了半小时——风里飘着小麦的清香,像极了13岁那年的春天。村口的老人认出他:“这不是高家小儿子吗?你娘当年天天在这等你!”那天,三个老兵的骨灰被埋进各自的祖坟,坟头的纸幡飘得很高,高秉涵对着土堆说:“老哥哥,到家了。”

这30多年,他跑遍了山东、河南、江苏,甚至新疆。有个四川老兵临终前拽着他的袖子:“我想回成都宽窄巷,闻闻老妈做的麻婆豆腐。”他就抱着骨灰坐3天火车,找到巷口的老房子,把骨灰埋在屋前的桂花树下——那一刻,邻居老太太端来一碗热豆腐,说“这是你叔当年最爱的味道”,他的眼泪“唰”地掉下来:“老哥哥,你闻见了吗?”

高秉涵的床头柜上,摆着个空骨灰坛——那是给自个儿留的。“等我走了,把我埋在母亲旁边,”他摸着坛身的刻字,“要刻‘高秉涵,山东菏泽人,13岁离家,90岁回家’。”可他还有个未圆的心愿:去年中秋看大陆高铁新闻,他指着“京台高铁”的规划图说:“要是能活着看到铁路通台北,我要坐第一班车回去——带着母亲的照片,从菏泽坐到台北,告诉她‘娘,我带您看我住了77年的地方’。”

采访结束时,高秉涵拿出本泛黄的笔记本,上面记着每一个他帮过的老兵名字:“张建国,济宁,1995年回家;李长河,开封,2001年回家;王顺发,徐州,2010年回家……”最后一页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:“乡愁是‘没做完的事’,我的事,是等一个‘九州同’的春天。”
窗外的台北雨丝飘进来,打湿了笔记本边角。高秉涵端起凉透的茉莉花茶——茶味里还藏着山东的麦香,像极了母亲当年的手艺,像极了所有老兵梦里的“家”。